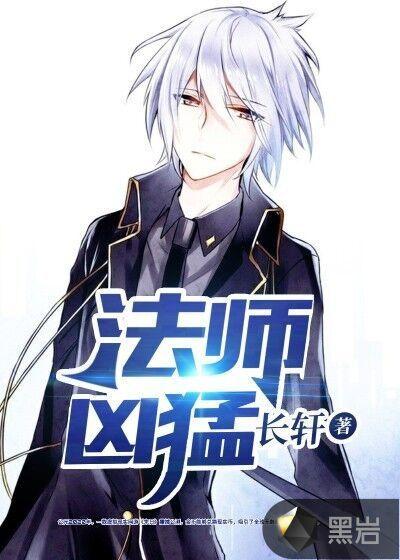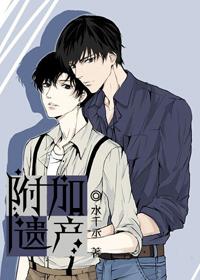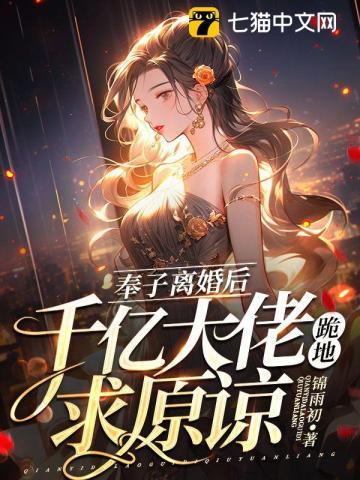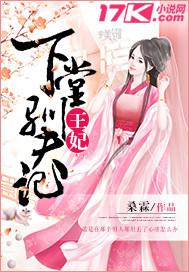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高平秧歌打酸枣(第1页)
8我过去没有接触过高平秧歌。去年赵瑜女儿出嫁,头天晚上,我和张发兄在赵家喝酒,席间,赵夫人袁嫂和她一班朋友唱了首高平鼓书《谷子好》。我虽不完全明白,但感觉歌词写得不错,瑜兄从旁告我,这是赵树理写的。因为宝卷经典句式是三三四,我对三字句开始的句子比较敏感。三三四句式,民间称为攒十字,是早期佛经翻译中留存下来的一种便于记诵的句式,后道教宣传最喜用,或与道教对汉语字句结构的认识相关。这个句式在汉语句法构词中有很大灵活性,易造词、易组句和易押韵。后来查《谷子好》原词,才发现主要是七字句,三字句只在开始用过两次。20世纪50年代初,赵树理写过一个高平秧歌《开渠》,可知他对高平秧歌非常熟悉。高平秧歌中有十字句式,我感觉这可能是宝卷句式的残存现象。不久,我在晋城一家网上旧书店见一册清抄本高平秧歌《打酸枣》,便购回细读。
此抄本为民间初通文字的人抄写,完全用高平方言记音,异体字和俗字很多,但大体还可读下来。抄本时间大约在清晚期或民国年间,虽是民间抄本,但从保存原始唱本和方言角度考虑,还不失其价值,虽有残破,多处已失字迹,但大体保存原貌。抄本除《打酸枣》外,另抄《游庵歌》,这是一个宝卷的变体唱本,基本用十字句完成。因抄本中多高平方言,我借助《高平秧歌》(高平政协编)、《高平方言词汇研究》(李金梅)和《高平方言词典》(冯辰生)等书,大致还原到今天的意思上来,失误肯定难免。对这个唱本略作解析,期待方家指教。
《打酸枣》在北方民间说唱中,有许多版本,山西各地,如晋中、晋北均有改编,直到现在还在流传,时见有人演唱。眼下流行的《打酸枣》主题是男女相慕,为常见民间文艺中的固定主题,多年流传不衰,因轻松活泼,诙谐风趣,始终受到人们喜爱。现在的《打酸枣》,较早期版本相对简单,角色也由三人减为二人对唱。民间文学流传似有一规则,即越早创作,生活气息越浓,后来变化在艺术上不容易超越原初创作。越早的民间文艺越不受官方意识形态制约,自由创作,言为心声,真情实感,发乎情,止乎礼。民间文艺随时代变化,但变化的特点是原生态生活被不断过滤,最后余下的只是原初故事主干,而其他与主干相生的原初生活丰富性,一般都消失了。我个人感觉,民间文艺,除特殊情况外,以保存原貌为整理法则,改编多是弄巧成拙。
我们现在可以推测一下《打酸枣》的创作灵感来源。为什么是“打酸枣”而不是“摘苹果”或其他?为什么北方民间姑嫂不和习惯在这个故事中转化为类似现代“闺密”的友情,等等。现在的《打酸枣》似一个爱情小调,已见不到原初北方真实民间生活情态,而早期流传的民间抄本中,还保留了原初的创作面貌,虽然我们现在很难确定《打酸枣》故事的最初来源,但较早的抄本,至少接近原始的故事起源。
《打酸枣》其实是一个成人故事。表面看,未涉男女之事,但故事前提建立在成人已有知识的约定之上,不须在故事中解释,不须特别说明,它保存在成人的基本常识中。作为故事逻辑起点,应当说体现了很高的文学判断,是对读者(观众)智力的尊重,它是一种预设了幽默前提的表现方式,即看这个故事的人,均明白故事建立的逻辑关系,它所有表达不离主题,自然融化在精选的情节中。民间文艺难免格调低俗,此为民间文艺常态,如太谷秧歌《叫大娘》一类,现在已很难流传。
但《打酸枣》不同,因为创作者找到了合理的故事逻辑,再加鲜活现实生活感受,无须借淫词媟语吸引观众。男欢女爱宜引人入胜,但文明习惯又忌直言其事,如何取譬借喻,非常考验作者的文学能力,分寸极难把握,《打酸枣》在民间文艺中是难得的有很高文学技巧的作品。
《打酸枣》暗含的故事逻辑是新婚嫂嫂刚过门,已有妊娠,但嫂嫂尚未脱少女羞赧,秘密只能和自己成年而未嫁的小姑子说。妊娠喜酸,是习见民间常识,创作者的灵感即源于此。“酸枣”是北方常见野生植物,恰与新婚嫂嫂处境建立逻辑关系,合情合理。“打酸枣”
本身即是一个隐喻,将“酸”转嫁到“打酸枣”上,比拟切适,是真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民间艺人观察生活之细密,非有些作家可比。请留意抄本中这两句“只听妹子打酸枣,为嫂酸水流下来了”,这是妊娠的正常反应;“为嫂有心打酸枣,还恐怕你的哥哥知道了”,新婚嫂嫂的感受,表达得恰到好处。因作者自信故事的合理逻辑,所以后面“打酸枣”的路上,依然依此照应故事潜在主题:“走了一沟又一沟,沟沟长的好石榴,为嫂有心摘一个,恐怕人家逮住了。”石榴结子,寓意多子多福,是北方民间风俗,足见创作者的匠心。
《打酸枣》另一个情节是嫂嫂为小姑子挑刺,文词是“叫嫂嫂,不好了。倒圪针把奴的手扎了”。嫂嫂为小姑子挑刺时,用婚后经验取笑小姑,借成人常识自然联想作比,稍失分寸,即堕恶趣,但这里处理得非常精妙。如钱锺书《围城》第七章写汪处厚,“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所以汪太太才“轻藐地哼一声,你年轻的时候,我———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钱先生再加一笔“汪处厚脸色一红”,这是钱先生暗写汪处厚性无能一例,也是建立在成人常识之上。
请读《打酸枣》里的文词:“左一挑,右一挑,倒圪针挑掉了。妹子生来是胆小,连个刺儿扎不了。妹子要是出闺走,新人房扎刺叫谁挑。妹子要是出嫁走,新人房扎刺叫嫂嫂挑。”正话反说,语语双关,体现中国文学创作中本来具有的含蓄传统。
抄本的最后情节是姑嫂“打酸枣”时,遇到二大爷家的长工小猫,取笑两位“花大嫂”。后多数改编删此情节,我以为似无必要。从戏曲角色考虑,小戏中如只有正旦花旦,而缺丑角,一定单调乏味。由故事逻辑设想,两个“花大嫂”遇不到男性,则演唱不会灵动。民间艺人具丰富生活经验及创造才能,设置这个丑角,一则表现长工及主家关系,小猫抱怨吃不好、吃不饱,这是北方农村真实生活,为一般雇佣制下常态现象。再则作者要借此角色表现农村生活场景,小猫取笑“花大嫂”,小猫唱“十奶奶”,均是有趣生活状态。有评论指小猫是流氓角色,调戏两位“花大嫂”,此为不谙民间文艺之言,如小猫是流氓,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不会用“小猫”或“小毛”这样温暖的称谓。有《打酸枣》改编本将丑角“小毛”与小姑配成亲的设计,可见这个角色的作用并非负面(《高平秧歌》,第16页)。小猫最后唱的“十奶奶”,或是晋东南民间文艺中曾有的一种表演套路,类似于宝卷及其他民间文艺说唱中常用的“哭五更”“十报恩”“十二月令”手法,借自然数顺序,表现丰富生活现象及传达各种教义,此种手法易记诵而又可容纳丰富内容,开合自如,兼有排比修辞效果,中国旧戏中有许多由此产生的变种,如“十不愿”“八不该”
之类,应是民间文艺中常见创造性艺术手法。
高平秧歌《打酸枣》虽短小,但可见早期艺人天然的文学智慧,从情节到文词,虽难称雅驯,但并不粗鄙。《高平秧歌》中所收《打酸枣》剧本,与早期抄本差异较大,虽角色相同,但对剧本立意似缺乏体会,大体是个诙谐的乡村小调,文词也较早期抄本累赘。
文学的自负是我们常以为比前人高明,其实是我们对前人的高明缺乏体会。
2020年7月10日于太原
(原载“古代小说网”2023年4月29日)
法师凶猛
...
附加遗产
雅雅走了,自杀。这个虽然跟他毫无血缘关系,但他毕竟叫了十多年姐姐的人,居然就这么消失了,并且给他留下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遗产,以及一个孩子。那年他才十九,...
微信游戏杀人事件
请不要用你的年薪来挑战我的零花钱,因为我一个月一千万零花钱!...
夫人别贪欢,傅总带千亿携子求入赘
盛以若与傅兆琛是假偶天成。她图他庇护。他贪她美貌。成年人的游戏取于利益,缠于欲望。三年情断。有人问盛以若,她和傅兆琛是什么感觉?身,心愉悦。有人问傅兆琛,他和盛以若怎么打发时间?日,夜贪欢。你我皆是俗人,应懂得难以启齿的往往不是感觉,而是感情。落魄美艳千金VS霸道矜贵阔少双洁1V1...
下堂王妃驯夫记
他是东临齐王,曾经叱咤沙场的战神,一场战事一个阴谋毁了他的骄傲她是安庆大将之女,一场背叛一场退婚毁了她的声名。一场上位者不怀好意的赐婚把本不该有交集的两个人硬生生凑到了一起,她一心保护好自己,但她只考虑到要怎么在那个男人眼皮底下安然脱身,却从未想过若是在那个男人那里丢了心该怎么办。她知道她无论如何不能替代他心中的那人,她只想他好好的。她倾尽所有的付出好不容易换来他一丝的怜惜,却在另一个女子的算计中一点点被磨光,她的心也在一次一次的伤害中渐渐冷了,之后他更是轻易被人挑唆认定她不衷,她终于心死离开,放两人自由。可总有人不愿放过她,想夺她性命永绝后患,多年后她再次回来时,又会书写怎样的爱恨情仇。...
一不小心潜了总裁
一本超搞笑的甜宠文曾是多个网站年度霸榜大爆文。出版名为大四女生林小溪在公园意外救下心梗老人,成了大佬全家的恩人,连大佬都得敬她三分!一世英名,毁于一朝进错房间,爬错床!从此开启了跟大佬先婚后爱,斗智斗勇的搞笑姻缘!第一次见面,暑假子公司实践,在电梯口将大佬当成维修师傅。结果从公司里涌出一群人恭敬道李总!第二次见...